您现在的位置是:网站首页>诗词理论诗词理论
赓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诗歌道路
《文艺报》2023-11-093346人已围观
简介江西诗派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流派,也是江西重要的传统文化标识。为更好地传承江西诗派的古典诗歌传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诗歌道路,推动新时代新诗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走向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象的广阔天地,《诗刊》社、江西省文联、江西省作协联合在北京举办江西诗派与新时代诗歌创作研讨会。l
赓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诗歌道路
——江西诗派与新时代诗歌创作六人谈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江西诗派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流派,也是江西重要的传统文化标识。为更好地传承江西诗派的古典诗歌传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诗歌道路,推动新时代新诗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走向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象的广阔天地,《诗刊》社、江西省文联、江西省作协联合在北京举办江西诗派与新时代诗歌创作研讨会。会上,施战军、谢冕、何向阳、李少君、张清华、张辉、孙明君、叶青、李小军、敬文东、杨庆祥、李遇春、王磊光、李啸洋、王悦笛、迟牧等专家学者就此展开探讨。现将部分发言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编 者
媲美唐诗的宋诗时代
谢 冕

我和江西有一段因缘,年轻时受邀到南昌参加江西谷雨诗会,那时我还年轻,做了一次讲座。当时有1万多字的讲稿,对当时诗歌的发展状况作了一些描述,没有什么高见,但这个记忆很深刻。
我前后长达3年在江西鲤鱼洲生活,写了一些应景诗,我自己不满意,但是很开心。有一首诗叫《扁担谣》,主要是批判自己。当时我在燕园生活很“个人主义”,感到深深的惭愧,进行了自我批判。这个诗很简单,是民歌体。北大俄语系教授龚人放和我一起上井冈山,龚先生是我的长辈,很儒雅。他说,谢冕,你把你的诗给我写出来吧,我要收集书法。我始终没有答应他。但我想过,要给龚先生写哪几句,因为诗很长,想到这两句:“月如镰,星满天,村头流水过浅滩”。
江西诗派在北宋徽宗年间,是连接北宋和南宋的一个诗人群体。我最近读了一些宋代诗人的诗,疑惑宋代怎么有那么多诗和诗人?毕竟唐代光辉的榜样在前面。现在讲苏轼,可以跟李白一起说。谁可以跟李白一起说?苏轼、陆游,都是宋代的。
一个流派的成立,理论家的推荐是非常重要的。吕本中一直在这么做,他的《江西诗社宗派图》中,有的诗人不是江西人,但和江西有关系;有的也不是特别著名的诗人,但由于这样一个学派的建立和理论家们的综合推介,于是他们留在了诗歌史上,有了一个和唐诗媲美的辉煌、伟大的诗歌时代。
我这里用了“时代”,就简单说说我对诗歌的审美要求。当然我的审美要求也从来没有断绝过,比如我认为“月如镰,星满天,村头流水过浅滩”,里头保留了一些诗歌的味道,但是我对自己的批判谈不上美。我信守诗歌的审美要求,有时候失去这个审美度量,我感到很惭愧。但能够留下“月如镰,星满天”,就是保留了诗歌审美的东西。
我更重视的是诗歌的时代性,诗歌和时代的关系。我特别不满意的一句话是,我们和时代没关系,我不代表任何人,甚至我不为时代代言。我一直说诗人就是先知、智者,先知和智者怎么能和时代脱钩?这个脱钩是不对的。诗人要表现个性可以,但和为时代代言不矛盾,为什么有一些诗人很反感这个表达呢?因为他们觉得诗人被代言得太多了,以为代言就是重复口号和标语,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在朦胧诗开始的时候,我很赞成朦胧诗诗人们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的特点。朦胧诗表现自我有革命性、挑战性,但如果走过头又不行,不能忘记根本。
诗人必须重视时代,为时代代言。艾青为时代代言过,牛汉也为时代代过言。最近我写了一篇短文章,谈牛汉的《华南虎》。《华南虎》写的就是一个时代,华南虎用尖爪在水泥墙上刻出了带血的诗行,这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这就为时代留下了印记。
张扬个性是对的,但不能脱离时代。我一直讲舒婷的《神女峰》,《神女峰》张扬了个性,也表达了时代精神。在女性不能自立的时候,《神女峰》出现了,“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能够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讲讲自己的痛苦或幸福,这是多么自由、多么了不起的场景。这就是时代给予我们的财富。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名誉院长)
文化传承发展的某种典范
李少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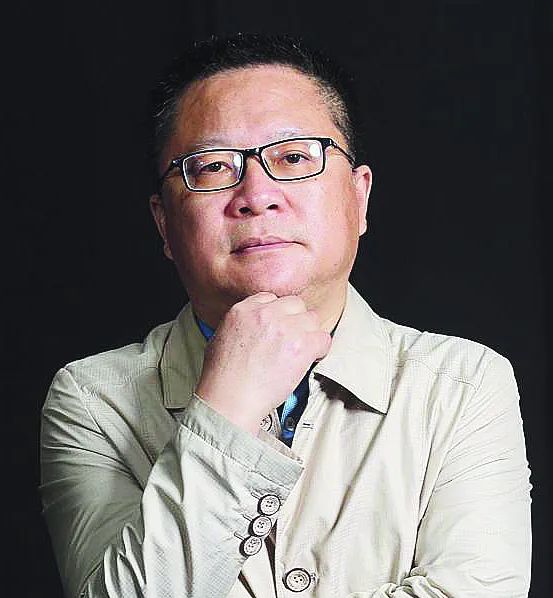
学习研究江西诗派,感触最深的一点,是江西诗派对前人诗歌的尊重、推崇和整合,对诗歌资源和文化遗产的态度。刘克庄在《江西诗派小序》称:“(山谷诗)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意思山谷诗是集大成。山谷就是北宋诗人黄庭坚,黄庭坚号山谷道人,和苏东坡有“苏黄”之称。黄庭坚推崇的诗法“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可以说是吸取优秀传统诗歌资源的极佳方式,是文化传承发展的某种典范。看重本来、注重当下、创造未来,就是诗词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宋代理学兴起,使儒家重新奠定主流正统地位。江西诗派推崇杜甫为“诗祖”,因为杜甫可以说是儒家的美学代言人,由于江西诗派的大力弘扬,杜甫经典地位至此完全确定。北宋文化被视为是一个顶峰。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唐代开放包容,兼收并蓄,道教成为国教,佛教全面进入中国,儒家一度边缘化。但宋代之后,理学崛起,儒家复兴,道教、佛教仍很盛行,才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形成文化高峰。苏东坡就是儒释道融合的典范,成为一个代表人物。士大夫在宋代成为一个阶层,是重要的社会力量。北宋士大夫阶层兴起的重要原因,就是对“理”的确立和追求,使得士大夫有了自主意识和主体性,有了一种新的精神、价值支撑,有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逐渐形成为一个独立阶层。
与之相适应,诗歌也在推崇“诗法”,江西诗派就特别强调“诗法”。黄庭坚等致力确立法则、推崇法度,讲究学问,“无一字无来历”,诗歌上师法杜甫,深究学问,寻求理趣。“法”自“理”派生出来,“理”就是精神、价值,汉学家宇文所安曾说:宋以后,作诗之“法”,以及在作品中观察得到的“法则”,变得特别重要。
江西诗派打破了诗歌的神秘性,不再盲目追捧所谓“天才”,强调诗歌可学,只有读书多才能得心应手。当然这也与北宋条件变化有关,印刷术提供阅读便利,“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有宋代能做到。江西诗派后期意识到仅仅强调诗歌的专业性以及技术修辞是有问题的,吕本中等又重视“活法”,重视人格修炼与境界提升,强调人诗对应、人诗合一、人诗互证。江西诗派不断求变,影响此后九百年。
江西诗派对新时代诗歌的启示,或许就是如何整合一百多年的新诗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提升、转化和创新,比如哲理性正是当代诗歌匮乏的,当然,更重要的是精神价值的张扬和突破。
(作者系《诗刊》主编)
江西诗派的启示与价值
张清华

关于宋代诗歌的评价应该如何看待,值得我们反思。这里头有师古的思维逻辑,也有正本清源而苛责当代的问题。这和我们这些年来不愿意承认当代诗歌的进步和价值,其实持有一个逻辑。新诗诞生一百多年,很多人依然不愿承认其合法性,认为古典诗歌才是正统,新诗是“非驴非马”;现当代文学界普遍推崇现代,贬抑和否认当代;我们这些搞当代文学的人,也很容易肯定20世纪50至70年代的诗,甚至肯定80年代的朦胧诗,但却不愿意肯定更靠近当下的诗。这是一种学术上的习惯和逻辑,似乎也很正常。
不愿意承认最近三四十年中当代诗歌的探索和进步,这个问题有两面性。一方面我们确实要反思当代,另一方面还要承认当代的“迫不得已的变化”,就是所谓的时代之变推动了文学本身的变化,尽管文学本身也有求变的内在需要,如刘勰所说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当代诗歌中也有这么一个逻辑。我们觉得最近三四十年,诗歌越来越背离原来言志抒情的传统,诗人们都普遍“羞于抒情”,为何?用严羽的话来说,眼下的诗歌就是“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诗人们竞相在诗歌里表现自己的知识、能力、观念、思想、主体性等,很少像前辈那样很自然地去抒发性情。
如果横向对比,会发现宋代诗歌和江西诗派中的问题与我们当代诗歌中的问题是接近和可以类比的。江西诗派中最重要的遗产,非常类似西方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留下的遗产,就是瓦莱里、艾略特、叶芝、里尔克、史蒂文斯这些巨匠,他们基本上可以说塑造了20世纪以来现代诗的基本格局和传统,成为最接近当代的“西方正典”。而后期象征主义与前期相比,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说理,以思想、知识、观念入诗。《荒原》如果不加注解,一般人根本读不懂,即使有人研究多年,假如对西方文化史、宗教史、诗歌史没有烂熟于心,仍是一知半解。《海滨墓园》《四个四重奏》也一样,这些诗歌已然成为现代诗、当代诗的传统。
如何看待宋代诗歌、江西诗派,其实还可以把眼光投向更广的地方。如果我们是宋人,面对唐代诗歌的群星灿烂与伟大气象,也是一样既感钦敬又有一种“影响的焦虑”,与其仰首膜拜,不如另择出路。参照20世纪以来世界诗歌的发展格局,或许我们对宋诗会有一个更客观的评价,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逻辑也会有一个更贯通的理解。
关于流派问题,江西诗派和历史上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不太一样。七子也好,七贤也好,指的是同一个时代的诗人群落,这批人有接近一致的风度和格调,有精神的呼应与生活的唱酬,所以被后人归纳为一个诗派。而江西诗派则更为复杂,诗人更多,生活的时间也有差异,是一种师承关系。另外江西诗派还意味着一种“地域”概念的自觉,有了空间区隔的意识。而在“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那里,基本没有什么明晰的地域文化自觉。此外还有师承文脉的自觉,关于“一祖三宗”,“隔空”学习和师承杜甫,以及非常清晰的文体、方法的自觉,在集群当中注重个性保持,等等。
江西诗派在意识上对于个体的注重,在总的认同前提下倡导凸显个人,这和现代以来的文学流派概念已经很接近,对于新时代诗歌的启示也是明显的。当下诗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地方性、地域意识的自觉,这对于诗歌写作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发明一个地域概念,对于诗歌批评和诗歌研究来说非常便利,也是一个学术贡献。我赞成据此提出“新江西诗派”的概念,这样可以对当代、特别是当下活跃的江西诗人,作出群体性的考察,或许会对我们进一步理解阐释当代江西诗人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作者系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看到热爱的诗人与诗派的“深处”
张 辉

今天参加这个会,我想起两本与宋诗、江西诗派有重要联系的书。我曾经长期阅读这两本书,它们是我的枕边书,也是旅行时经常随身带的书。一本是钱锺书的《宋诗选注》,一本是潘伯鹰的《黄庭坚诗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学史既是文学写作的历史,也是文学选集、文学传播,特别是文学解释的历史。钱锺书与潘伯鹰对黄庭坚的不同解释,也许对我们今天在古今关系中思考江西诗派与现代诗学的关系有所帮助。
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对江西诗派、尤其是对黄庭坚的评价,或许是个人化的,不无偏颇的。文学史上乃至书法史上,我们通常将“苏黄”并称,但《宋诗选注》中,钱锺书选了18首苏轼的诗,却只选了3首黄庭坚的诗,分别是《病起荆江亭即事》《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以及《新喻道中寄元明》,三首中只有最后一首诗直接与江西有关,是写给他哥哥黄大临的。钱锺书不仅在序言中对晚清时黄庭坚的集子卖过十两银子一部这样的“辣价钱”多少有些不解乃至不屑,而且在介绍黄庭坚的部分说了下面这段话: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老人……他是“江西诗社宗派”的开创人,身前跟苏轼齐名,死后给他的徒子徒孙推崇为杜甫的继承者。自唐以来,钦佩杜甫的人很多,而大吹大擂地向他学习的恐怕以黄庭坚为最早。(《宋诗选注》,钱锺书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10页)
我们引述钱锺书先生这段话,当然不是要苛责他非常具有个人偏好的判断,更不需要将之视为不可更易的定论。我自己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常常想到另外一些文学解释史的例子,其中最常想到的是西方文学史上歌德与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截然不同的评价。对歌德,乃至对整个“狂飙突进”一代人而言,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是“神”一样的存在;而对托尔斯泰而言,莎士比亚尤其是他的《李尔王》,却是完全不足取的存在,可以说全盘否定。这就是解释史的事实,同时也构成了文学史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对江西诗派、对黄庭坚乃至对宋诗的理解,也应该——或许,也不能不——建立在对这样的解释史的“同情之了解”之上。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对读潘伯鹰《黄庭坚诗选》中的下面这段话:
……山谷在宋诗中,是一个特出的大家。他的诗在当时已经与苏东坡隐若一敌国。因之影响所及,学他的人非常之多。而当时吕居仁画出“江西诗派图”,甚至推他像个大主教一样,从而生出“江西派”这样的名号出来。名号既立,毁誉遂多。(《黄庭坚诗选》,潘伯鹰选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页)
今天讨论江西诗派的当代意义,在古今对话的前提下讨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这样的语境中,对读钱锺书和潘伯鹰这两本书,至少可以有两点启示。首先是,我们不要把热爱的任何一位诗人、任何一个流派,推为“大教主”或将之神圣化。对我们所热爱者,甚至尤其需要有勇气、有独立判断的精神,对他们的不足之处、不到之处,加以识别、分析与批判。这也许依然是一种带着热爱的批判,但我们恰恰不应该放弃这种批判的意识。其次,无论如何,我们要像潘伯鹰先生所提示的那样,真正看到热爱的诗人与诗派的“深处”,“搔着他的痒处”,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细读他们的诗。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所所长)
创造新境界 缔造新诗派
孙明君

江西自古地灵人杰,诗风繁盛。江西诗派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地域命名的诗文派别,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江西诗派虽然彪炳史册,但已经成为历史,新时代需要建设新的江西诗派。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灵魂,是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以下我主要就效法黄庭坚、创建新江西诗派谈点看法:
一、黄庭坚以唐诗的集大成者杜甫为学习对象。《瀛奎律髓》中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江西诗派提倡学习诗圣杜甫的诗歌创作。杜甫志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创作了“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诗史之作。黄庭坚《与王观复第二书》中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在《答洪驹父书》中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以上观念一直影响着后人。
二、黄庭坚积极向同时代的优秀诗人学习。黄庭坚以苏轼为师,与苏轼并称“苏黄”。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黄庭坚坚信苏轼忠君爱国。在苏轼被贬期间,黄庭坚始终持弟子礼。黄庭坚积极与同时代诗人交流,组织领导了江西诗派。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中说:“曰江西宗派,其源流皆出豫章也”。黄庭坚的人品和才华吸引了众多诗人,在黄庭坚的引领下,江西诗派内的成员常常通过集会、结社、书信等方式进行交往。江西诗派的影响遍及整个南宋诗坛,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三、儒释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庭坚的思想以儒家为中心,同时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也占一定比重。据专家统计,其诗文中共引《庄子》典故700多处。受道家思想影响,黄庭坚在人生观、思维方式及处世态度上,看轻仕宦、安时自适;黄庭坚虔信佛教,喜好禅宗。他受到佛禅思想影响最大的是般若思想与禅宗的心性论。有学者指出:受到了庄子齐同万物的思想,又吸收了禅宗思想和儒家的反身内省的方法,黄庭坚形成了“万物一家”的思想观念。
四、江西诗派是以黄庭坚诗创理论为中心而形成的诗歌流派。黄庭坚诗歌理论中最著名的主张是“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无一字无来处”,他主张要“以俗为雅、以故为新”“随人作计终后人”“我不为牛后人”。黄庭坚的诗歌遵循创作规律,敢于尝试变化,形成了风格奇崛、法度严谨,说理细密的风格。黄庭坚主张用字“要字字有来处”;提出“诗眼”说,他称为“句中眼”,可谓“置一字如关门之键”;提倡“句法”,黄庭坚《送顾子敦赴河东》云:“无人知句法,秋月自澄江”。他倡导“当官莫避事,为吏要清心”“不以民为梯,俯仰无所怍”。他的《流民叹》等诗歌深刻描写了社会现实、民生疾苦。
在江西诗派之前,魏晋时代有千古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近代有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陈三立及其子陈寅恪先生。在创建新时代江西诗派时,我们有必要弘扬陶渊明、黄庭坚等古代诗人的思想和创作,在继承前人精神的基础上,创造新境界、缔造新诗派。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开掘江西诗派诗学资源
李遇春

在中国文学史上,宋代的江西诗派和明代的公安派可谓影响深远。如果说黄遵宪、柳亚子和郭沫若等早期新诗诗人更多地传承了晚明公安派的诗学,这一条道路得到了学界不断的研究和深化,那么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诗传统对中国现当代诗歌(无论新旧)的影响则就严重地被低估和忽视了。这正是新时代倡导和激活江西诗派传统资源的意义所在。
毋庸讳言,江西诗派作为一种绵延不绝的中国诗学传统,其文学史地位和价值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被严重地遮蔽了。从我有限的视野来看,在近现代旧体诗坛,江西诗派的作用实在太大了。一代又一代的江西籍旧体诗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无论是旧体诗词创作还是诗学理论建构,都留下了灿烂而珍贵的文学遗产。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同光体宋诗派首领陈三立在近现代旧体诗坛是巨人一般的存在之外,也不应忽视,作为《学衡》杂志主要发起人和学衡派代表性诗人的胡先骕是江西人,甚至学衡派诗人阵营中还有许多江西诗人都有深厚的诗歌家学渊源,如陈氏父子(陈三立、陈衡恪、陈隆恪、陈寅恪),王氏兄弟(王易、王浩),都是素有令名的文学世家。他们在新诗革命背景下依旧坚持守正创新,在学习西洋文学的同时不废中国诗歌传统血脉,为中国诗歌传统的复兴保留了文化种子。随着《学衡》杂志办刊难以为继,在九·一八抗战背景下,又一个江西诗人陈赣一挺身而出,他领衔创办了全国性的旧体诗文杂志《青鹤》月刊,一直坚持到1937年被日本人炸毁最后一期稿本而被迫停刊,又一次在国难当头延续着中华民族传统诗学的命脉。此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江西词学大家龙榆生还先后创办了大型旧体诗词期刊《词学季刊》和《同声月刊》,为中华诗词的现代传承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不难发现,在习惯上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如果撇开固定的新诗流派史视角,转而从旧体诗词流派史来看,在那个“三十年”里,从《学衡》杂志诞生了学衡派,从《青鹤》杂志产生了青鹤派,再到《同声》及其同声派,已然构成了一个大体清晰的中国现代旧体诗歌流派史脉络,而江西诗人及江西诗派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可惜长期以来,我们囿于新诗一家独尊之偏见,遗忘了这样一条现代旧体诗词流派史脉的存在,而这种不断强化新旧对立的学术偏至于今亟待矫正。在新时代语境中,我们需要大力倡导新旧融合而不是新旧对立,大力弘扬守正创新而不是割裂传统。在新时代如何开掘江西诗派的传统诗学资源,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崭新课题。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文艺报》2023年10月23日第8版。
上一篇:字字珠玑屈原精神延续 ——漆雕世彩新著《楚辞集联》序
下一篇: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