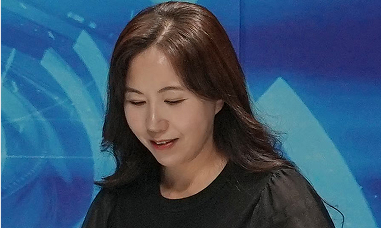您现在的位置是:网站首页>散文家散文家
王宗仁
作者2023-10-1215004人已围观
简介王宗仁,当代散文家,作家,陕西扶风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

王宗仁,当代散文家,作家,陕西扶风人。1957年毕业于陕西省扶风中学。1958年应征入伍,历任汽车七十六团政治处见习干事、书记,青藏兵部宣传处新闻干事,总后勤部宣传部新闻干事、宣传组组长,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主任,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7年中学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任汽车教导连学员、汽车驾驶连副驾驶员、文化教员和营部文书、团政治处书记等。1964年调任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新闻干事,1965年调任总后勤部宣传部新闻干事。1988年后任宣传部创作组创作员、创作室主任,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
1955年在《陕西文艺》发表散文处女作《陈书记回家》,2010年散文集《藏地兵书》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迄今共出版散文、散文诗和报告文学专集31部。散文集主要有《传说噶尔木》 《雪山无雪》 《情断无人区》 《苦雪》 《拉萨跑娘》和《藏羚羊跪拜》等代表作品,报告文学《历史在北平拐弯》等。
作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汽车兵,他度过极其艰苦危险的年轻时代,四十多年来一百二十多次翻越世界屋脊唐古拉山,用自己的命与青藏高原交心。他见惯了死亡,多次亲眼见到自己的战友兄弟离他而去,于是他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怀恋英雄,歌颂壮烈而美丽的死。藏羚羊之死只不过是他悲壮作品中的一篇。王宗仁现在是中国散文学会秘书长,安家北京,但他总觉得生活在内地有哪点不对,他总想着高原,脑海中总浮现出那雪山冰湖蓝天的样子。有许多年轻时戎马高原的内地人像他一样,把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留在了高原。以后不管身在何方,总觉得青藏高原才是永远的故乡。于是许多到过青藏的人都怀疑,那里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摄持了汉地游子的灵魂。
这种神秘的力量有一部分其实就是来自过去年代的英雄主义和壮丽牺牲。王宗仁感到这种精神在现在越来越少,越来越不被重视,于是他越来越依恋高原,越来越只要一有可能就扑向高原。
一百二十次翻越唐古拉山创造了一个文人、一个军官、一个作家的最高纪录。这当然也把当下时髦的自驾车、拉萨八廓街淘什物的红男绿女远远甩在后面。上天见怜那些认真的、贫苦的、有责任的人---最开始他是用命去认识高原的,他是中国最无望的人---农民讨生活而去高原的,他用穷人的腿走高原。他当然很有资格不屑那些带着氧气袋上高原的白领们和现在许多附庸风雅的作家艺术家。
1958年,王宗仁告别秦川的父老,带着一个求生存图发展的梦来到部队,没想到分到这样一个严酷恶劣的地方当汽车兵。他很懊丧,总想着能够逃离"鬼地方"。
五十年代的天非常冷,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低温下,王宗仁穿着满是油污的破军袄,驾驶着德国二战时的大卡车。渴了吃一口雪,饿了拿出冻硬的馒头,歪在硬椅背上睡一觉,一个月也洗不上一次热水澡……
每天早上冒着极度严寒走出屋的第一件事是烤车。这种老爷车,没有马达,没有启动机,有的车一夜不能熄火,早上烤车一个多小时---否则车子开动管子就会憋断……王宗仁手冻得跟馒头一样,还要到高原上去挖红柳根,用来烤车。稍长,他明白这是破坏最脆弱的环境,心很痛,但是没办法。
1953年,他刚14岁,还是小学6年级学生,就成了家里相当壮实的一个劳动力。就在与乡亲们边锄地边聊天的过程中,他走进了一个既陌生又神奇的生活领域,并萌发出写点东西的念头来。他把生活中一件真实的事情,实实在在地写出来,成为一篇散文习作《陈书记回家》,冒昧地投寄给了当时的《陕西文艺》杂志,谁知竟在1955年第8期上发表了。王宗仁把这篇散文称为"锄头刨出来"的处女作。从那以后,他又陆续在县报、省报上发表了一些新闻稿件,都是在田里劳动时用锄头"刨"出来的,用现代的时髦语言说就是采访。在此期间,他在扶风县中学读书时,又在《陕西日报》"秦岭"副刊上发表了《两麻袋玉米棒》、《离娘的骡驹谁养大?》、《赵大爷》等散文,成为县上颇有名气的小作家。1957年初中毕业,因为他爱读书能写稿,村上让他担任长命寺小学民办教师。同年年底他应征入伍,奔赴青藏高原。
走进青藏高原的人都知道,这儿是冰雪的世界,是没有绿色和鲜花的生命禁区。但对王宗仁来说,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赋予了他生命意志和生命存在的深度和强度。"走进西藏,也许你会发现理想;走进西藏,也许你能看见天堂。走进雪山,走进高原,就走向了太阳"(《走进西藏》歌词),他真切地感受到这里是他生活、创作和人生的摇篮。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为了走向大海,才来寻找昆仑山。"入伍后,他在汽车团当驾驶员,开着从德国进口的载重量6.5吨的大汽车,每年都要至少6-7次地翻越海拔5300米的唐古拉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往返于甘肃---青海---西藏;祁连山---昆仑山---唐古拉山。从1958年到1964年,在那儿整整奔波了7个春秋,吃的苦不少,尝到的甘甜也很多,特别是他的文学创作热情也升华到了极高的境界。
开上一天的车,浑身像散了骨架似的,保养完车辆,就到了夜晚,正是战士们休息的黄金时间。但王宗仁却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他要把一天的见闻写下来,否则吃饭不香,睡觉不宁。为了不影响战友们休息,驾驶室就成了他的写作间。打开工作灯照明,写到夜里12点或1点钟,此时的雪域高原万籁俱静,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存在,陪伴他的只有想象中的文学女神。有时写完天已微亮,索性就趴在方向盘上迷糊一会儿,醒来打起马达又出发。天天这样折腾,身体十分乏困,但开上车竟然没有出过事故。这时期他创作的一系列散文、诗歌,先后在《人民军队报》、《高原战士报》、《解放军报》、《青海湖》、《人民文学》等报刊上变成了铅字。其中,他的散文代表作《考试》,1964年2月8日在《解放军报》发表后,获得总政治部第一期征文优秀作品奖。当时他仅25岁,是团里的干事。团政委王品一拿着奖状自豪地说:"总政治部给一个普通干部发奖状,这在我们团的历史上是头一回。"他由于文学创作成绩突出,被青海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脚印是路的基石。纵观王宗仁最初的文学之路,他的步伐迈得是那么的坚实,不仅写出了富有特色的雪域高原上的军事美文,而且更好地走出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从驾驶员到团队文化教员、营部文书、团政治处书记、青藏办事处新闻干事,他的工作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真是青藏高原上的苍天啊,也不负苦心之人……
王宗仁曾说:"一个作家的文学长廊应该是五彩缤纷的。"
1965年,解放军报社要举办全军第9期新闻干部学习班,上级点名通知要让王宗仁参加。半年的学习之后,他被调到总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任新闻干事。当时王宗仁是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青藏线的,他感叹道:我虽然身子离此地远了,但心更近了,因为我是昆仑山上的一棵草!
王宗仁酷爱文学,也偏爱新闻,一开始写作,文学和新闻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与他结伴而行。他曾经形象地对同行们说:"在我的肩上拉着两套'马车'。八小时之内写新闻,八小时之外搞创作。"正因为这样,他在从事新闻工作长达8年的时间里,尽职尽责,为总后勤部增添了许多新闻亮点。例如他先后采写报道的"毛主席的好战士年四旺"、"川藏线上十英雄"、"当代优秀大学生的楷模---张华"、"优秀的科学家---黄翠芬"、"中年知识分子的榜样---王湘生"、"青藏高原模范干部---张鼎全"等先进典型人物,在全军、全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他们均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至今让众多的新闻同行和人民群众记忆犹新的关于张华典型的报道。八十年代初,第四军医大学学员张华奋不顾身跳进粪池救老农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此事传开后,很多人议论说:大学生救老农不值得……因而一时也没有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王宗仁得知此事后,急忙赶赴西安和张华的家乡黑龙江等地,深入群众,认真采访,冷静分析,认为张华的举动闪烁着时代的光芒: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索取,而在于奉献……张华事迹报道"一炮打响",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此后才有了被我国新闻界称为"张华现象"的一系列报道。笔者曾参加了许多新闻作品研讨会,人们都要把此篇报道作为经验性的总结,传教于青年新闻工作者,希望他们在采写新闻中注意运用和借鉴。
1982年,经过30多年的追求与攀登,王宗仁终于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会员。他又开始主攻报告文学、散文与诗的创作,但仍不放弃新闻写作。他忘不了尊敬的文学前辈。作家严文井,曾当面给他讲过的这句话:"新闻和文学是亲家,分不开啊!你搞新闻工作可以经常下去,接触群众,熟悉生活。搞创作长期坐机关是不行的。"对这句话,他坚信不疑。这些年来,他坚持采写了30多篇报告文学。其代表作《写在她远行的路上》(与马继红合写)发表后,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张光年称赞它写得像诗一样的美丽。这篇作品荣获了中国作协"第一届优秀报告文学奖"。对此,王宗仁深有体会地说:我在被采访者面前,是以通讯员、记者(是3家报刊的特约记者)的身份出现的,但是当我搜集素材时,我却用创作报告文学所需要的材料来要求自己,到生活中去挖掘,去索取。其结果不仅使我顺利地写出了通讯、消息,也为我进行报告文学的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样才会有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图书奖以及总后勤部第一届军事文学奖的长篇报告文学《历史在北平拐弯》。此书长达29万字,由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出版,也是被列入国家"七五"计划的重点书目,已经印刷了两版10次达15万册。《中华老年报》、《大连时报》、《深圳特区报》等多家报纸纷纷连载,以满足读者需要。荣获中国图书奖和解放军图书奖的《睡狮怒醒》,长达27万字,分别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和台湾日臻出版社于1995年同时出版,可见此书的读者群是何等的广泛。曾荣获"505"中国报告文学奖的《周冠五与首钢》一书,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后,该社和总后政治部文化部在京联合举办了作品讨论会,文艺界和经济界40多人参加了研讨,热情赞扬了此书是一部描写改革和改革带头人的精品之书。作为评委的文学前辈、著名评论家陈荒煤大加赞赏说:"这是一部真正写工业改革的书。"
1996年后,王宗仁突然有一种感觉,后半生要做一件大事,书写青藏线上的兵营生活、壮美的风景,要表现出一种不朽的高度---中国军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英勇顽强的精神风貌,文学创作上追求一种新的文体---"大特写"、"大散文",用散文的笔法写报告文学,表现出青藏高原上的人情美、境界美、苍凉悲壮的自然美……
对军旅作家王宗仁来说:他从昆仑风雪中走来,还要回到昆仑山上去,因为那里掩埋着700多名军人的遗骨,有些还是他生前朝夕相处的战友,在他眼里永远是最壮美的风景线。他去此地就像女儿回"娘家"一样,都是轻装简行,坐汽车进藏,重走青藏路,获得新的发现,新的感悟……
望柳庄
我常常觉得在我的生命深处,有一些什么东西在荒芜地漂流,使我无法平静。怀念或是感动或是遗憾?
昨天的叶子没有枯萎。
此刻,2004年早春的这个早晨。昨晚一场雪使昆仑山的天地变得很完整。但是即使到了白天,山下的格尔木也像入睡。春天的寒风挤满窗棂,窗外稍远一点的地方,那棵柳树正在费力地摇动,分明想摆脱大风的束缚。可是不能。
这样的时刻,我在稿纸上写下三个字:
望柳庄。
它有一段埋藏得很深的秘密。关于春天的秘密——一位将军在飞雪的戈壁滩播种春天的故事。
有山脊却看不见山,有村庄却不住人。只有这片柳树年年月月像遗忘了季节似的迎着风沙摇晃卷曲,枝条交错成各种形状。即使这样,它依然寂寞。
这时,一位中年军官来到柳树前,望着树枝许久,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我真恨不得割下耳朵,挂在柳树的肩膀上,让它听听有多少人编写了多少赞美它和它的主人的故事。
这个军官就是我。
我北京的书房就叫望柳庄。这个名字常常使我想起从前,想起从前我就觉得吃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可是,格尔木的望柳庄依然很寂寞。
不少人都是通过我的笔端知道了格尔木城里这个望柳庄。然而,谁能想到那时候格尔木根本算不上城,格尔木就有个望柳庄。望柳庄就住着将军和一伙修路的兵。
格尔木是修青藏公路大军在昆仑山下的第一个落脚点。从那时起,这儿就叫望柳庄。后来,望柳庄就成了修路的大本营。再后来,公路跨上世界屋脊,望柳庄所在地格尔木就成为内地进入西藏的咽喉。如今的格尔木是青海省第二大城市,青藏高原的名城,是国家命名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可是,谁人知道格尔木起始于望柳庄?又有几人知道是谁在望柳庄前栽下了第一棵柳树?
五十前的那个初春,昆仑莽原上仍然是弥漫的风沙卷着雪粒、石子在狂吼。世界混沌一片。春天在何处?
这时,一位老军人攥着一棵柳树在敲格尔木冬眠的门:醒来吧,我要给你换新衣!
说毕,他挥镐挖土,栽下了第一棵柳树。
这不是一棵孤零零的树。这片世界从这儿开始,跟来了一大队树的队伍,一棵挨一棵地跟着这棵树排起了队。
这个老军人就是慕生忠将军。其实他并不老,四十四岁能算老吗?
格尔木的树来自湟水河畔。
修路队伍离开西宁途经日月山下的湟源县城时,慕生忠让汽车停在一片苗圃前,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些刚刚冒出嫩芽的苗苗不放。许久,他对管树苗的人说:买一百棵。随行人员不解,问:政委,咱只管修路,买树苗做啥?
慕生忠时为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长兼运输总队政治委员。修青藏公路了,他又成了总指挥。大家一直习惯叫他政委。
慕生忠听了这问话,瞪了那人一眼:你说做啥?扎根安家嘛。我们是第一代格尔木人,格尔木是先有人还是先有树?不,人和树一起扎根,这根才扎得牢靠!
格尔木,一片荒野,风沙怒吼。
一个惊呼上当的小伙子问慕生忠:我们要做第一代格尔木人,可是格尔木在哪里呢?
小伙子还没把话说完,一阵风沙就把他吹了个趔趄。慕生忠说:年轻人,告诉你,我们的帐篷扎在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
说着,他一锹铲下去,沙地上就铲出了个盆状的坑坑。格尔木的第一棵柳树就栽在这坑里。
一百棵杨柳苗,都栽在了刚刚撑起的帐篷周围。一共两大片,杨柳分栽。第二年,这些小苗大都落地生根,绿茵茵的叶芽把戈壁滩染得翠翠地叫人看着眼馋:它们一路狂奔的长势一天一个样儿地蹿长着。给它喝一盆水它长个头儿,给它喂一把肥它也添叶。
看把将军喜的,他像大家伙一样咧着金豆牙笑得好美。快乐的老人,他当下就给两片树林分别命名:“望柳庄”和“成荫树”。
有人问:政委,你这名字有啥讲究?
他哈哈一笑:望柳成荫嘛!
看,他还是钟情望柳庄。
将军的笑声糅进了柳的躯体里,树又蹿了一节个头儿。
广漠的戈壁滩荒芜了数千年,现在猛乍乍地生出了这两片绿茵,自然很惹眼,也醉人。毕竟是柔弱苗,难与漠风对峙。常年的飞沙把它浸染得与沙地成为一色,人站在远处就难以瞅见,有时它索性就被那气势汹汹的褐石色盖住,淹没了。
好在,它不服,顶破沙土,又伸起了腰杆。
它的根茎部连着一片阳光。
我第一次看到望柳庄的情景至今难忘。那是令我失望的一次发现。当然失望之后我滋生了更强更多的企盼。这片柳林活得很艰难也很缠绵。
那天午后,我从拉萨执勤回到格尔木,车子刚行驶到转盘路口就抛锚了。其实这地方离我们军营顶多一公里路,可是车子耍起了脾气卧下不动,我也不能回部队只好陪着它。当时风沙很大,迎面扑来人连眼睛都睁不开。助手昝义成回军营取所换的零件。
风沙越来越大,我无法承受它的无情撕打,便顺势走向路口的地排平房,站在了房檐下。风沙果然小了,身上也暖和了许多。这时我举目一看,门楣的三块方砖上刻着三个字:望柳庄。字用红漆涂过,格外醒目、我的心一下子滋润了,好像在风沙世界里望见了一片翠绿的草地
也就在这时候,我才发现平房前的沙滩上横七竖八地半躺半立着一棵棵树苗。这就是将军带领大家栽的那些柳树,有的已经被沙土埋得不见真面目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在我的感觉里,它们仍然是亭亭站立的硬汉子。
望柳庄前的树站在冬风和春风之间。它们要告别寒冬实在不容易,要把春天迎来路途也蛮艰难。然而,大海不会老去。望柳庄前怎能没有柳树?
后来,我才知道这三个字是慕生忠将军亲笔题写。
我长久地不错眼珠地望着这三个字。高架桥点亮了星河之灯,昆仑山的世界突然变得亲切。我的眼前仿佛开满了鲜花。
风沙还是那么大。
可它绝对吹不落我心中这片春天的世界。
这就是我第一次看到望柳庄的前前后后。好些天后,战友们告诉我,次日清晨,当风沙停止以后,慕生忠带着同志们把那些倒地的柳树苗一棵一棵都扶了起来,培好土。他边收拾这残局边对大家说:吹倒一次,咱扶起它一次。吹倒一百次,咱扶它一百次。直到它可以结结实实地站在沙滩上为止。
柳树是远方来的移民,在将军爱抚的目光里它忘了惆怅和家乡,克服了水土不服的娇气,格尔木成为它的第二故乡。
瀚海孤树,林中一木。
有几棵树只绿了短暂的生命,就消失在戈壁滩。
它们死了。
这似乎是预料中的事,但人们还是觉得太突然。
它们没有来得及留下遗言……
又是一个烈日暴晒着戈壁滩的午后。我出车归来,路过望柳庄。我有意停下车,要看看那三个字:望柳庄。这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了,每次从雪线上回到格尔木,必然在望柳庄前停一下,这样我的灵魂就得到了自由,就有一种从黄昏走进晨曦的美好感觉。
可是这一次破例了,一片隐晦落在我心头。
我看到望柳庄前不远的戈壁滩上,一群人围着一堆土丘,默默静立,一个个低着脑袋,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
我上前打问。竟然没人理睬我。几缕阳光从云头上泻下,照射在土丘上,很有几分燥热。不过我很快就看出来了,那土丘是一个坟堆。
埋的什么人?
我又向一个人打问,他仍然不理睬我。我好生奇怪。便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一起默然地站立着,心中的疑团越挽越大。
弄清真相是后来的事。原来在头天,望柳庄前有三棵柳树死了。当然不是无缘无故死去的。这地方缺水,少氧,干旱,寒冷,其中哪一样都会把这些移栽而来的幼苗置于死地。戈壁滩的树,活下来的是强者,死去的也绝不能说是孬种。
骆驼驮着夕阳走在不归的路上。
慕生忠把三棵死去的柳树掂在手中,端详几番又几番,仿佛永远也看不够。未了,他说:“它毕竟为咱格尔木绿了一回,让我们这些饥渴的眼睛得到了安慰,是有功之臣。现在它走了,我们难受,怀念它是合情合理的。不要把它随便扔在什么地方,应该埋在沙滩上,还要举行个葬礼。”
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土丘,独特的柳树墓。
戈壁滩上第一个醒来的人是寂寞的人;第一棵死去的树呢?人们没有遗忘它。
常有格尔木人给那土丘浇水。其实浇水的人想法很简单,这些树也像人一样,躺在戈壁滩会口干舌燥。浇一瓢水,让它们滋润滋润。树要喝水,就得有人递给它。
谁也没有想到的事发生了。人们有心无意浇的水,唤醒了死去的柳树。到了第二年夏天,土丘上冒出了一瓣嫩芽儿。那芽儿一天一个样,由小变大,由低变高。
啊,柳树!
这是从埋葬着三棵树的坟墓上长出的柳,是一棵死而复生的柳,是将军用怜悯的心唤醒的柳!
后来,人们就把这棵柳称为墓柳。
经过了一次死亡的墓柳,活得更潇洒更坚强了。青铁的叶子泛着刚气,粗褐的枝干储存着力量。大风刮来它不断腰,飞沙扑面它不后退,寒冬腊月它依然挺立。死里逃生的战土最显本色,最珍惜生命。
墓柳接受过无数路人投来的目光,这目光多是赞许,也有不以为然的嘲讽。嘲讽什么?嘲它孤独?讽它清高?不得而知。它继续着它的轨迹活着,藐视一切懦弱者地活着。
时间年年月月地消逝着。望柳庄前的柳树种得越来越多,树片越来越大。它们和墓柳连在了一起,混为一体。已经分不清哪棵是墓柳了。
在望柳庄生命的进程中,这肯定是个生辉发光的日子。那是青藏公路通车到拉萨后不久,彭德怀元帅来到格尔木,就住在望柳庄。彭老总的名字在青藏线上被人们神话般地传颂着,这当然与慕生忠将军有关,与修青藏公路有关。当初,国家没有把修青藏公路纳入当年计划。慕生忠修路时遇到了财力人力的困难,他便找到了老首长、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彭老总刚出国抗美援朝回来,他对慕生忠说,我回国脚跟还没站稳,手头没钱。这样吧,我把你的修路报告转递给周总理,让他解决你的问题。就这样慕生忠得到三十万元的经费。彭老总还给慕生忠调来了十辆大卡车和十个工兵,一千二百把镐,一千二百把锹,三千包炸药,才使修路工程开展起来。
现在,彭老总来到了格尔木,他不住那座专为他修的二层小楼,却和慕生忠一起住进了望柳庄,延安式的砖拱窑洞里。将帅的心相通。这一夜,美酒和春宵……
柳树的枝儿碰醒了杨树的梦。
彭老总:你们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在柴达木的戈壁滩上建起了一座新城。这个地方是大有希望的。
慕生忠:没有彭总你的支持,我是不行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格尔木人都感谢老总。
说话间,彭老总让人拿出一瓶好酒,对慕生忠说:人生做事就要有你们把公路修到拉萨的这股劲。猫在屋里不出门是干不成大事的。来,今天我敬你一杯
人称慕生忠为“酒司令”,“昆仑酒神”。他浑身豪气,一腔爽笑,以至他的粗暴过失,都带着酒的精神。难怪人说这四千里青藏公路是他用酒打通的。
彭老总敬酒,这是慕生忠没有想到的。他
端起酒杯,连干三杯。还要继续喝时,彭老总把酒瓶拿开了,说:“你这酒鬼,再喝就醉了。我不想让你喝醉,还要你干事。”
慕生忠说:“谢谢彭总,我已经喝好了。你有什么任务就下达吧。”
彭总走到墙上挂的中国地图前,右手从西北甘肃敦煌方向往西南角上一划,说:“这一带还是交通空白,从长远看,是需要修一条路!”
还是慕生忠在北京请求修筑青藏公路时,彭老总就提到要修格尔木到敦煌的公路。慕生忠照办了,在青藏公路修到可可西里时,他就派工程队修通了格敦公路。现在,彭老总又提起了这件事,慕生忠如实地告诉彭老总:
“我们已经在格尔木到敦煌之间修起了一条简易公路,下一步我们把它修成一条正式公路。”
彭老总高兴了,又端起酒杯,说:再敬你一杯。
这一杯下肚,慕生忠真的醉了……
彭老总来到格尔木的第二天,就离开望柳庄,在慕生忠的陪同下,乘车南行踏上了青藏公路,一直上到海拔四千六百多米的昆仑山口。车过纳赤台养路段,彭老总在昆仑泉边遇到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小孩,他把孩子抱起高高举过头顶,满含希望地说;你是昆仑山的第一代儿童,你的名字就叫社会主义吧!
慕生忠听了彭老总的这活,勾起了他深切的回忆。五年前就是在这个昆仑泉边,修路大军被阻挡……
彭总见慕生忠走了神,就戏说他:
“你是不是又在想把这昆仑泉水变成酒潭才好?”
“没有。我是想那年修路到了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昆仑河真够难为我们了,为了架起青藏公路上的这第一座桥,我们想了多少办法,付出了多少代价!桥架起后我们把这桥叫天涯桥。那真是天之涯海之角啊!不久,陈毅元帅进藏路过昆仑河,是他把天涯桥改名为昆仑桥。这名字改得好!”
彭老总说,他是个诗人,我们这大老粗肚里可没这么多墨水。
当夜,两位将帅返回格尔木,仍然投宿望柳庄。他们肯定又推心置腹谈了许多,这是私房话,别人无法知晓。但是,有一点传出来了。慕生忠对彭老总说,谁都有见马克思的那一天,他说自己百年之后,就安葬在格尔木,这样能天天望见昆仑山。他这一辈子什么都可以舍弃,就是离不开格尔木,离不开昆仑山。彭总听了,爽声一笑,说,你这个慕生忠,想那么远干啥?好好活着,把格尔木建设成柴达木的大花园,好好活着!
慕生忠生命的进程严格地按照他的设计完成。
1994年10月18日,八十四岁的慕生忠将军在兰州与世长辞。10月28日,将军的九位子女护送着他的骨灰,踏上了昆仑山的土地。在昆仑桥上,二儿子把将军的遗像安放在桥头,大儿子从车上拿出两瓶平时老人最爱喝的皇台酒,启开瓶盖,面对昆仑山,双手恭恭敬敬地把酒瓶举在头顶,说:
“爸爸,你在世时,为了你的身体,每次你喝酒时,妈妈总是背着您在酒里掺矿泉水,请您原谅。爸爸,今天您回来了,您就喝喝这醇香的家乡酒,敞开喝吧……”
昆仑桥在颤抖,昆仑河在抽泣。
随着将军的骨灰洒向高天,昆仑山忽然飞起了漫天的雪花,天地皆白!
此刻,覆盖着积雪的望柳庄格外庄严,神圣……